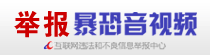我写批评,纯属偶然。几年前,我心血来潮,于小说创作之余,写了几篇评论文字,在《黄河》《阳光》等刊物发表,同道中人多有好评。这种好评直接促成我由小说创作向评论写作的转向。到2018年,我几乎中断了小说创作,竟一门心思做起文学评论的事情。我的评论作品散见于《黄河》《阳光》《延河》《长城》《齐鲁学刊》《中国文化与产业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中国煤炭报》《山西日报》等纸质刊物以及“山西文学院”等一些较知名的网络平台,计50余万字。评论《族天下与氓世界》(2012年发表于《黄河》)和《“响水”:诗意的汁液》(2020年发表于《阳光》)分别获得第七届、第八届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。
说到批评观,我有过只言片语的表达,但以前从未写成文章。现在拾取二三话语,稍作梳理,展开阐释。
第一句话,评论工作者是一名专业的读者。在自己的一篇评论中,我曾做过这样的表白:“我更愿意让我的批评成为一次‘延伸的阅读’。”又一次,在接受采访时,我对自己的评论工作者身份做过自况:“评论家其实是一名专业的读者。”“延伸的阅读”和“专业的读者”,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层面:前者是就阅读行为而言的,后者是从言说主体出发的。我这样说,绝非故作姿态,而是出于一个基本事实:评论工作者当然是读者。但这位读者,较其他读者,可能更饶舌,更痴情于文字,更富有表达欲。我坚持评论者的读者姿态,既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掂量,也反映了对时下文学评论的不满。我以为,一位评论者要写出好的批评文字,必得摘去“高屋建瓴”的高帽,摒弃“指点江山”的妄念,放下大而无当的抱负,不用大概念蒙人,不用大架构唬人,先做一名诚实的读者,从细读文本开始,去收获最真切的感受。我以为,这不是废话,而是一个写好评论的前提。
第二句话:争取把评论写得好看一点。文学评论要不要好看?提这个问题,好像故意找茬。坦白说,我读到的评论文章,好看的不多,说它们枯燥无味大体不错。不在少数的批评工作者,以贴标签替代文本分析,用概念化内卷评述,将教科书中专业术语搬来搬去,把本该生动的文学写作变成一种无法卒读的现代八股。其实,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写作传统便有好看的义项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钟嵘的《诗品》、金圣叹批《西厢记》、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,甚至宋人的书论画论,都无不文采飞扬。外国批评名家的评论也是非常好看的,哈罗德·布鲁姆的《影响的焦虑》、米兰·昆德拉的《小说的艺术》,都让人一册在手,不舍得放下,何尝有一点枯燥的学究气。
文学评论固然是一种论,但这论必须有足够的文学欣赏经验来支撑。它首先是一块鲜活的文学绿地,而不是理论的灰色区域。我在两栖写作中深刻体会到:评论者与小说作家、诗人的创作冲动是一样的,都来自对诗意的敏感,都受到审美情趣的驱使,都贯注着深刻的个人经验,都把对形象的体味作为构思和书写的出发点。但文学内部的分工,却让文学批评越来越游离于创作,“批评分明算得上是创作的孪生兄弟,却越来越变得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人。非但唆使它们彼此分家,还把它们分别归属于两个相距甚远的区域,一个进入崇尚直觉的艺术领域,另一个却被派作是理论世界的公民”(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语)。我以为,在文学评论中,概念是无法替代审美分析的,理论框架的构建也不能取代文本分析,文学所蕴含的“理”决不是凭据逻辑思考就可以获得的,而过度依赖学术标签、学术用语为文只会让文章变得了无生气。文学评论既需要有敏锐的感受和深刻洞见,也一定要有文学的淋漓元气,有漂亮的文字。我将它称作“好看主义”。坚持做到:宁散漫,勿严谨;宁滋味,勿唯理;宁片羽,勿圆满,以随笔式的评述取代理的推衍。2021年,值鲁迅先生《阿Q正传》发表百年,我写成《屏蔽记忆·阿Q禅·共同相》一文。该文在某刊发表时标为“文学评论“,而在山西文学院平台转载时却标为“随笔”。我以为,这小小的标签差异,却是对我评论风格作出的最好诠释。
第三句话,评论好否取决于一个人的学养。写下这句话,心不免忐忑,这不是变相地说你自家有学养吗?我当然不认。但我话中却显然留了让人诟病的漏洞。其实,我是坦露一个事实。我写小说、写散文,也写诗。但我最大的爱好不是写,而是读。也就是说,我是一名真正的读客。我从1979年开始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。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,有时数月半年不写作品,却无一日不读书,且什么类的书都读,文学的、哲学的、历史的、心理学的、社会学的、生物学的、科学的。读得有了感触,就会在书扉、书眉、书脚加上批注评语,或随手记在本子上;多则一二百言,少则三五十字。今日想来,我由创作转向评论,或不是一时兴起,而是长期的读和批的延续。数十年阅读、写作和思考,让我积累起较丰厚的学养。我的评论尚可一读,只怕得益于这些积存的学养吧。我以为,与创作相比,评论可能更依赖于学养的润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