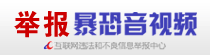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唐代“红地翼马纹锦”纹饰复原图。
作为中国文学中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,“马”始终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图腾之一。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,是文人墨客情志的寄托,更是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身,在诗行词阙间踏出了一条跌宕而璀璨的意象长河。
马之初入文学,便带着鲜明的实用印记与礼制色彩。《诗经》涉马之作所在皆是,将其嵌入了周代社会的肌理。《小雅·采薇》以“四牡翼翼,象弭鱼服”八个字,勾勒出军人的威武雄壮;《周南·汉广》“之子于归,言秣其马”的吟咏,让良马成为婚嫁礼仪的象征;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中“执辔如组,两骖如舞”的描摹,将男人狩猎化作勇武精神的生动注脚。此时的马,是“甲兵之本,国之大用”的现实载体,“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,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”(《汉书·马援传》),在田猎、征战、典礼等各种场景中,搭建起早期文学中马意象的根基。
渐渐地,马挣脱了实用的桎梏,升华为精神境界的象征,为文学注入了新的审美维度。支道林“重其神骏”(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)的论断,将马从役用之畜提升至精神品鉴的层面;杜甫笔下“锋棱瘦骨成”(《房兵曹胡马诗》)的胡马,以“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”的形神刻画,赋予骏马“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”的忠勇品格。这种“神骏”不仅是外在体态的矫健,更是内在精神的投射——它是穆王命驾八骏、驰驱千里(《穆天子传》)的开拓气魄,是曹植连翩西北、视死如归(《白马篇》)的少年豪情,是李白酒后弄刀(《白马篇》)的侠客风骨,让马成为英雄人格与理想精神的具象化身。
而当理想与现实碰撞,马又化作文人怀才不遇的共鸣。屈原“乘骐骥以驰骋兮,来吾道夫先路”(《离骚》)的宣言,让骏马成为政治理想的引路者。韩愈在《马说》中发出“衹辱于奴隶人之手,骈死于槽枥之间”的喟叹,将千里马的埋没,比作贤才在古代昏庸世道中的沉沦。李贺“何当金络脑,快走踏清秋”(《马诗》)的叩问,则借良马待伯乐的境遇,道尽了寒士渴望用世的内心焦灼。这些诗句中的马,不再是单纯的物象,而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镜像——它们或瘦骨嶙峋而自带铜声(李贺《马诗》),或拳毛欲动而徒思边草(刘禹锡《始闻秋风》),在悲戚与傲骨的交织中,完成千里马最动人的精神升华。
在边塞诗的雄浑旋律中,马又绽放出别样的壮烈之美。岑参笔下“马毛带雪汗气蒸,五花连钱旋作冰”(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),以战马的酷寒境遇,衬出征人的无畏;王昌龄“骝马新跨白玉鞍,战罢沙场月色寒”(《出塞》),用战马的静默,诉说征战后的苍凉;王翰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(《凉州词》),更让马成为戍边生活的见证者,在“醉卧沙场”的洒脱与“征战几人回”的悲壮间,承载起家国情怀的重量。这些马,是“弓弦抱汉月,马足践胡尘”(骆宾王《从军行》)的战场伙伴,是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(陆游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)的精神图腾,它们的蹄声,踏过了长城的烽烟,也踏成了民族记忆中最雄浑的交响。
马还构成了古代诗文中不可或缺的送别意象,承载着离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与不舍情怀。“一鞭残照里”(王实甫《西厢记》),马鞭挥落的是故园回望的不舍;“古道西风瘦马”(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),踽踽瘦马是天涯漂泊的孤寂。它驮负着离人远赴塞北江南、蹄声叩响长亭短亭的别绪;它见证着征人戍客的聚散、鬃毛飞扬边塞风沙的苍凉。从“挥手自兹去,萧萧班马鸣”(李白《送友人》)的喟叹,到“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”(岑参《逢入京使》)的仓促,马嘶与风吟交织,尽写人间的别离与牵挂。
千年诗行,马蹄声从未远去。从礼制之仪到精神之魂,从壮志凌云到悲怆孤鸣,从边塞壮歌到送别离情,它早已超越物象本身,成为华夏儿女精神世界的鲜活注脚。铁骨载丹心,骏影映千秋,这匹跨越千年的文学之马,将在笔墨间继续驰骋,承载着民族的情志与风骨,踏向永恒的文化长河。